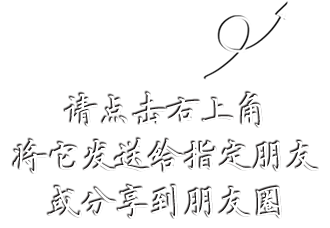●钟琼珍
从院子这头走到那头,也就两百来米的样子,院子的这头有一棵树,那头也有一棵树。
院子是狭长的,南北走向,上午的时候,东边的楼挡住了阳光,院子里不热,很舒适。我的杂物间刚好在院子的中段,先生在杂物间门口放了两张有靠背的红色凳子。下完楼梯,我在凳子上歇息一会儿,就开始往南边这一头走,我走得很慢,其实我是想走快一点的,但快不了,我的脚下还是虚的,腰间别着尿袋。但这样我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与南面的这棵树对视。
南边的这棵是非洲楝,树枝肆意地向四周伸展开来,柔美缱绻,像极了婀娜少女舒展的手臂,略显尖长的叶子缀满了枝干,绿得诱人。这是棵柔弱的树,哪怕是一只小麻雀在枝头打个尖,都能让整个枝条颤上老半天;这又是棵活泼热情的树,哪怕是再细微的风儿吹过,无数叶片便使劲儿摆得欢。这树是多情的,而我也多情,我总觉得它这雀跃是给我的,它在为我欢呼,为我加油,于是我这脚步便不再那么凝滞。每次走到树下,我都会停下来,与低垂的叶片握个手。
我再慢慢地往回走,我要走到凳子那儿,坐着歇息一会儿,再站起来往北走。这时候,我就能越来越近地看到北面的这棵大叶榕了。这是一棵伟岸的树,树干很直,恒定而凝重,宽厚的深绿色叶片紧紧簇着枝干。树静静地立在那儿,不动也不言,显得很肃穆,我总觉得它像一位刚劲的中年汉子,已入不惑,所以将自己隐没在沉寂里。我还是会默默地跟它握个手的,我用手捻着它垂下来的长长的美髯,想到岳飞,想到关羽,我试图从他们的美髯里获取力量。
走累了,我坐在两棵树的中段——红凳子上歇息。微凉的风吹来,很惬意,在我的正上方,是一块长方形的图画,这变幻莫测的图画令我着迷。我看到澄澈的湛蓝底色的图画里,一不留神就长出来一朵白云,然后是两朵、三朵,像是平地开出来的花,让人心生欢喜;有时候这图画成了晒谷坪,坪里密密匝匝地铺满了棉花;不知啥时候又成了秋收后的田野,被辛勤的农夫们犁翻过来,一垅一垅的真好看;也有时候,不知谁拿了笔,蘸着云,在蓝色布幕上乱画一气,浓的淡的粗的细的。好些时候,我看到太阳和乌云在打架,我从乌云缝隙里透出来的射线可以想见它们的战斗有多激烈,我明明看到太阳已经把乌云驱赶到边上,却不知乌云们偷偷搬了救兵,转眼间又占领了整版画面,如此几番拉锯,最终要么晴空万里,要么乌云密布。我是偏向于太阳这一边的,总是在这拉锯中一叹一喜,直至决出胜负,便也认了,不再理会,因为我知道,哪怕是乌云密布,或是倾盆大雨,也会有雨过天晴的那一刻。
先生每天搬出来两张红凳子,大部分时候,另一张红凳子也坐着人,不是夏便是汇,汇还兼着输送绿色蔬菜的职责,大袋子一张开,里面赤橙黄绿,瓜瓜菜菜全是自己种的。她们轮番陪我聊天,或者我累了时只听她们讲。以前只顾着往外蹦,院子里的邻居们大多不认识,这会儿我这形象一下子成了全院子的中心。开初,邻居们只是用关注的眼神看着,不太敢靠前搭话,后来家婆的一个旧识小心翼翼地上前问候,我倒是很轻松地跟她说了状况,估计我这态度让她放了心,传了开去,于是乎每天都有不同的邻居前来,关切地询问,更多的是温暖的鼓励。玉姐睡眠不好,我与她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戒助眠药的体会,我们相互鼓励,共同设定每天的步数目标,为各自的进步而欢欣雀跃;一天,赖叔在后面追上我,说我走路快多了稳多了,他都看着开心呢,这一刻暖在心里,酸在鼻头;上午的时候,保卫室门口一溜排开的是五个九十岁以上的老人,有时候我会坐在第六张凳子上,听她们讲家长里短,讲过去的苦难和现在的幸福,甚至听她们淡定地讲有那么一天终将离去。我觉得自己像贼一样,不但拉低了整体的平均年龄,还偷到许多人生的智慧。
人的一生,有头也有尾,终究是一个线段,而这线段,又由许许多多小线段组成。从这棵树到那棵树,这是一个特殊的线段,它让我懂得刚柔相济,让我懂得感恩,让我在歇息之后,有更大的勇气朝前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