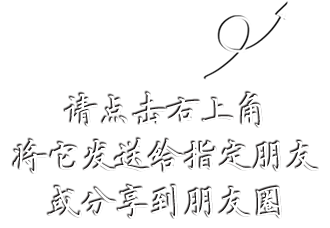●蔡巧玲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大多数家庭是孩子多,房子少,除了父母及祖父母带小孩睡外,几个大些的堂兄弟姐妹挤一张床睡是司空见惯的事,家里如果实在挤不下,去别人家搭床睡(客家话,意指寄宿、借宿)也习以为常。
我小时在老家是跟祖父母睡的。7岁到平远差干后,虽然父母有工作,但只分得一个房间,一张铺板床。床没有围栏,四周得把蚊帐压在草席下,父母把才几个月大的弟弟护在中间,我蜷缩在墙边的床尾。小孩子睡觉不老实,常常会把蚊帐掀开,那年代蚊子多,我们被咬几个小包包没关系,可早上起来弟弟就成了“小花脸”了。
看来,得让我去别人家搭床睡才好。母亲首先选择了比我大1岁的邻家女孩,她父母早离婚了,祖母去世不久,家里只有父女俩生活,屋虽破旧,但有两间一厨房。孤独的女孩,晚上有个同龄人作伴也挺开心的。
究竟一起住了几个月我记不清了。但忘不了在夏天的一个晚上,我先上床,摸到床中间湿湿的,她把煤油灯拿前一看,竟然是一堆老鼠屎尿,便赶快叫她爸来。她爸看后说:今晚你们不能睡这床了,跟我睡吧。于是我们就转移到她爸床上去。她爸把靠墙这边让给我们,自己转到另一边去,谁知那装谷壳的烂枕头一移动就漏谷壳了,虽作了清理,但总觉得身上还有谷壳刺人,我整晚都没怎么睡。
母亲只得帮我找下家。她得知银行有个伯伯的老母亲从梅县来小住几个月,有单房,我就跟她住了几个月。她叫吴伯婆,对我挺好的。
吴伯婆要回梅县了,母亲就想到关系较好的陈阿婆。陈阿婆家中有儿孙几口人,她和一个比我大5岁的孙女菊姐一起睡。老床四周有床栏,即使挤了点人也不容易掉下来,她欣然答应了。我本来就喜欢菊姐,能每晚和她一起很开心。她爸是开药店的,人很随和,经常会拿几片甘草给我当零食。他有满肚子的故事,我们经常缠着他讲故事。他除了讲善恶有报的故事外,也会讲些妖精鬼怪的故事,听完上楼睡觉时,我和菊姐都不敢先行,生怕黑咕隆咚的楼上会突然窜出个“鬼”来,只好怯怯地跟在拿煤油灯的陈阿婆身后。
夏天很热时,我和菊姐就在床边地下(木板楼棚)摊一张席子睡。有次醒来发现就我一人在床下,问菊姐怎么回事,菊姐说:我半夜听到“鬼”叫,吓死了!叫你又叫不醒,我就自己爬上床了。陈阿婆说那是猫打架(求偶),不是鬼。我才舒了一口气。
后来菊姐去30里外的仁居读高中住校了。此时恰巧有个比我大三几岁的英姐到缝衣店做学徒,晚上师傅们都回家了,只有她一个人住缝衣店,正好需要有人作伴,我就离开陈阿婆,去英姐那里搭床了。
那时缝衣店设在街尾,一楼裁缝,二楼除了后面用木板隔有两个小房间外,其他地方空荡荡的放了点杂物。侧面有个小门,出去便是山,山边有一个用木板搭的简易厕所。我们晚上几乎不用上厕所,但还是免不了有特殊情况发生:一个寒风刺骨的半夜,英姐说肚子痛,要上厕所,实在没办法,她捂着肚子,我打着手电筒,两人壮着胆子开了门。也许是手电光惊动了附近的狗,“汪汪汪”地吠个不停,在这寒风吼叫的野外,瑟瑟发抖的我恨不得也钻进厕所里去……
有一个雨季,连续几天下雨,本来就溪涨河满了,那晚又大雨滂沱,半夜就水浸街了。师傅们过来把衣车(缝纫机)和橱柜等扛上二楼后都回家去了,我和英姐继续睡。待天亮起来,发现洪水已封门,我们只得站在吊脚楼的阳台上看水。整条街已成河,街尾和差干河连成一片汪洋!幸亏水没上二楼。后来是父亲单位两个叔叔撑来木排,把我俩从阳台上接下去,我们才得以回家。
直到我14岁,母亲又换了工作单位,我们搬到老街门楼上住,总算有了可以摆两张床的房间,我终于结束了晚出早归的“搭床”岁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