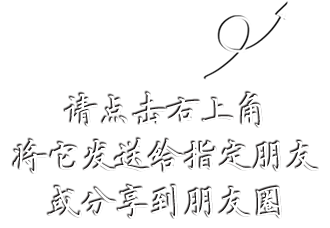兴奋之余,发现家中木柴存量已经不多。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,第二天我就跟随本屋冉娣嫂、纪祥哥上山砍柴。天未亮就吃完早饭,三人沿着平远石正通往兴宁黄槐的古驿道,从狮子寨、猪嫲岃、三间茶亭(现存残墙断壁)的台阶拾级而上,到达莲花山北面的柴山。放下柴落(装柴的工具,多为竹制),各砍各的杂木柴。我虽然年少,手起刀落中杂木柴已经砍好,剩下的要砍成小段装进柴落。我贪图省力,把杂木的一头架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,右脚架住杂木,手起刀落,冷不防柴刀一弹,刀落在我的右脚二趾,现出白骨,鲜血缓缓地流了出来,这时我就懵了。在旁边的纪祥哥急急忙忙地找来大青叶,边包扎边呼叫冉娣嫂。见此情此景,他们决定救我要紧,送我回家。他们手忙脚乱地装好已经砍好的柴,我的柴刀、柴落装在冉娣嫂的柴担上,由她快步回村里告诉我的母亲(其时父亲是国营工人,不在家);纪祥哥采取背我一段路,挑其柴担一段路的方式背我慢慢下山。就这样,背一程挑一程,我一点一滴的血迹滴在青石板上,上山又下山,艰难地越过了山顶茶亭。
母亲接到口信后,急忙带上背带、红药水,步履如飞地越过第二间茶亭来接我。见到母亲,我万千思绪涌上心头,流出苦涩的泪水长叹道 :“未能帮上忙,倒是连累家庭。”母亲身手敏捷地从兜里取出布条、红药水,换下缠裹在我伤口上的手巾、青藤、青叶。又用背带罩住我,背起我,一步一台阶缓缓下山。有道是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,背着近80斤重的人下山崖,母亲的艰辛可想而知。而她边下山边喃喃道:“这次,我会被你爸爸骂死,耽误了你出远门。”我伏在母亲肩膀上遐想,善良厚道的母亲就是一座伟岸的山。豆大的汗珠顺着母亲的脸颊往下淌,湿透了衣衫。
下午1时多,母子两人终于回到了家。当然“广州大串联”是去不成了,由于缺医少药,加之伤口感染,我40多天后才痊愈。
(陈胜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