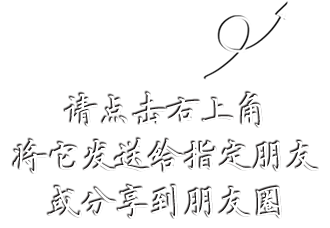●黄育兰
星月皎洁,明河在天,四无人声,声在树间。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如是语,道尽了此刻窗前的岑寂。
窗外,一轮圆月正从江对岸的黛色山峦后缓缓攀起,清辉无声地漫溢开来,温柔地拥抱着山峦起伏的暗影。这是小城独有的景致,在看似局促的格局里,藏着一段开阔的山水;于简朴宁静之中,蕴着化不开的缱绻柔情。这柔情丝丝缕缕,悄然牵动了心底尘封的画卷。
幼时居住的老屋背靠大山,面朝韩江水。犹记得那些溽暑将尽的黄昏,暑气未散,蝉声渐歇。大伯劳作归来,洗净手脚,便会搬出那张被岁月磨得光滑的小方桌,几只矮凳,安放在门前的青石坪上。桌上不过几碟寻常小菜,盐水毛豆、腌渍萝卜皮、或许还有一小碟酱猪头肉。他旋开那个磨得锃亮的小锡酒壶盖,小心翼翼地斟上一小盅白酒。山水为伴,晚风轻拂,这是他一天中难得的松弛时光。我们姐弟几个,平素对父亲的威严心怀敬畏,嬉戏玩闹总隔着距离。唯独大伯,待我们极是慈爱。每当他准备小酌,总会笑呵呵地招呼我们围拢过去。那碟子里油亮诱人的肉片、喷香的花生米,他总先稳稳地夹起几筷子,放进我们的小碗里,看着我们吃得香甜,他眼角的皱纹便舒展开来,像盛开的菊花。后来我曾笑问他喝酒的“讲究”,他眯着眼,带着几分自得的惬意,演示给我看:先是极珍重地抿上一小口酒,让那辛辣的暖意在舌尖喉头流转片刻,才不慌不忙地伸筷去夹菜。若那下酒菜——比如一块卤得透亮的猪耳朵——块头大了,他必用那双竹筷耐心地将其在碟中翻覆,戳成适口的小粒。有时还要推到碟底的酱汁里浸润一下滋味。那夹起的食物,总要在碗沿内侧轻轻一磕,仿佛仪式般,滤去多余的汁水,这才慢悠悠地送入口中,细细咀嚼,喉间发出满足的轻叹。这份从容的惬意,常伴着门前柳梢头悄然升起的月亮,持续到夜色渐浓。
大伯干的是重体力活,营生不易,忙起来便没了定时定点,一日三餐常常囫囵对付。外出做工时,饿极了,几口烧酒压一压饥肠也是常有的事。待身体发出警报,那难以吞咽的哽噎感日益明显时,已是食道癌晚期的噩耗。再见他,是在出院回家的第一天。住院多日,他清瘦得颧骨高耸,面色是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,昔日炯炯有神的双眼因消瘦而显得格外大,却黯淡了神采,像蒙了尘的旧玻璃。即便如此,看到我来,他枯瘦的手仍急切地比划着,喉咙里发出模糊的音节,执意要去买菜留我吃午饭。他是灶台间的好手,小时候,我总爱在他家厨房门口探头探脑,只要嗅到锅里飘出不同寻常的香气,不等他唤,我已早早捧着碗筷,眼巴巴地守在饭桌旁了。然而自那日起,我再也没能坐在那张小方桌旁,看他怡然自得地抿着小酒,分享他碟中滋味各异的下酒小菜了。大伯离开时,刚过完六十二周岁生日不久,他襁褓中的小孙子还未能清晰地唤出一声“爷爷”。弥留之际,他已说不出话,只是极其吃力地抬起那只枯柴般的手,对着围拢的亲人,虚弱地摆了一下,然后紧闭双眼,缓缓地、沉重地摇了摇头。出殡那日,阴云低垂。姑姑望着棺椁,声音哽咽破碎,反复低语:“我再也没有大哥了……”我双膝跪地,叩首拜别,那积压了太久的、混杂着无尽悲伤与无能为力的巨大洪流终于冲破堤防,哭声与泪水倾泻而出,淹没了周遭的一切。
大伯与伯母待我视如己出。我出嫁那日,他们拉着侄女婿的手,絮絮叨叨,千般叮咛万般嘱托,字字句句皆是“莫让她受委屈”。我生头胎时,他们早早备好了柔软的小衣裳,攒下了一篮篮最滋补的农家土鸡蛋,伯母更是隔三岔五就托人捎来问候。满月酒宴上,大伯小心翼翼地抱着襁褓中的婴孩,伯母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,仿佛怀里抱着的是稀世珍宝,满眼都是化不开的慈爱暖意。大伯走后,每次回娘家,我总要去看看独居的伯母。不久,伯母也病倒了,距离大伯去世尚不足一年。接踵而至的打击,让这个本已支离破碎的家更是雪上加霜。堂哥们强忍悲痛,不忍再让她忧惧,只含糊地告诉她,是些“炎症”,吃药打针就会好。
待到十一月中旬再去看她,她已缠绵病榻。一见我进门,浑浊的眼中倏然亮起微弱的光,挣扎着要从床上起身。我赶忙上前,轻轻握住她那只因病而肿胀变形的手,冰凉而沉重。扶着她,感受着她每一步挪动都耗尽全身气力,脚下虚浮如踩棉絮。苦难为何如此残忍,偏要一次次碾过这已然孱弱不堪的身躯?心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,阵阵发紧,几乎透不过气。彼时,她的精神已极度委顿,意识也时常陷入模糊。吞咽功能几乎丧失,只能勉强咽下些流质。堂嫂端来一碗熬得细糯喷香的瘦肉粥,我接过来,在床沿坐下。舀起一勺,轻轻吹凉,小心地送到她唇边。粥汤不时从她无法闭合的嘴角蜿蜒流下,我一遍遍用纸巾轻柔地沾拭。看她费力地嚅动嘴唇,极其缓慢地吞咽,喉结艰难地滚动。我轻声问:“伯母,好吃吗?”她迟缓地转动着迷茫的眼珠,目光似乎要努力聚焦在我脸上,半晌,才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“嗯”。这一声轻应,瞬间刺穿了我强撑的平静,酸楚汹涌直冲眼眶,我慌忙别过脸去,泪水已无声滑落。她反倒吃力地翕动嘴唇,微弱地吐出几个字:“莫……莫多想……吃……吃药……就……好了……”接着,又断断续续,含混不清地向我絮叨起一些关于神佛、关于魂魄归处的零碎故事,那些她深信不疑的慰藉。这微弱的光景,短暂得令人心碎。此后的半个月,病魔骤然发威,摧枯拉朽。剧烈的疼痛日夜折磨着伯母,将她最后一丝生气也残忍地榨干。她如同风中残烛,灯油熬尽,在一个寂静的凌晨,悄然熄灭了。接到堂哥电话的那个清晨,听筒那端尚未出声,那长久的沉默和压抑的呼吸声已如重锤击落心口——我的大伯母,挣脱了尘世的苦痛,随大伯到天上团圆去了。那晚,夜空中,一轮圆月清冷孤悬,光华满地,仿佛无声的送别。
今夜的窗前,星月依旧皎洁,明河亘古在天。一朵云飘过檐下,夜,亦缓缓地深了,寥落的情绪铺陈在灯下。以诗,以梦,怀抱月光,尘世这样美好又忧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