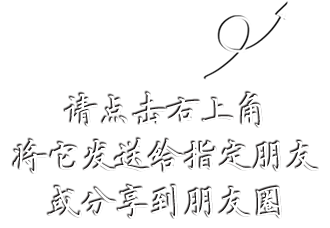●陈桂峰
一行人来到长东寻味。
他们来到长东饭店,从城里的烟火,到山里的烟火,便完成了转换。长东饭店的味道,只有食客知道。
这里离县城有一段距离,全程青山绿水,水泥路贴着石窟河,蜿蜒钻入山林深处。长东饭店坐落在半坡间,坐北朝南,一横杠黑瓦白墙的房子,新粉刷的白粉难掩年久的凋残和风蚀。屋门前是长长的禾坪,有露天的也有搭了棚子的,间隔着摆了几张圆桌和凳子,就是客人吃饭的地方,有几分懒散,也有几分土气,这就是长东饭店。
店里的狗叫阿黄,是我们所熟悉的,老远就像风车一样摇着尾巴。这伙人在禾坪里落脚,东张西望,追逐着山鸟,目光在绿海里起落。大山阻塞了他们的目光,只留下西南一个缺口能望得远。一溜望去,石窟河、红色泥土长黑树的山坡,轻纱朦胧的山头,有几只像竹蜻蜓转着风叶的风车,有人说那是平远县的风力发电风车。此时的夕阳陷入了云絮,涨红着脸烤得西天似火烧般的灿烂。东边的山矗立耸天,好像一件蓑衣挂在天幕,把长东分割在西边。仰望的人越发渺小、卑微。南边的山就不同了,由近到远慢慢升高,树木长得比较杂,杉树、松树、榆树、桐树、枫树……禾坪下面的山坡是梯田式的农家菜地,除了四时蔬菜,还有柚树、桔子树、李树等。
拍着景色,夜色就像蜘蛛从四处爬出来了,爬上了路,爬上了禾坪,爬上了桌子,也爬上了脸。饭店的特色菜焖鸭肉也上桌了,香味飘荡,牵扯起味觉。鸭肉是用农家土灶烧山柴做的,鸭子是山上野养的,灯光下油黄锃亮,很抓眼球。这是今晚的主打菜,也是长东饭店一年四季的主打菜,客人却从不腻味。山里的四时季节,四时的柴火,烹调了四时的味道。喝着野生茶,另一些臣菜,野木耳、野韭菜、野蕨菜、红背菜、豆腐,有时还有咸菜焖猪肉,一一上桌亮相,长东饭店的味儿就齐了。
他们讲得来是因为文学,聚会也是因为文学。因此,长东的鸭肉宴就成了文学围炉夜话。他们是黑暗里唯一的光,照亮着四面,打趣、逗乐、隐语、豪言、诗情、梦想,机锋迭出,连屋北的松树和禾坪边的树枝都拢过来偷听。有先生睿智过人,啃个鸭头也生造出“典故”,众文友毫不留情打脸。风起诗人的诗意,李杜瞬间飘然而至。筷子上的哲学,下圆上方,人间造化凭谁说。舀一勺子汤,却把马尔克斯、伍尔芙、奥康纳、门罗等等,当作汤料喝光了。但他们谦虚,心胸此刻正像黑咕隆咚的山谷,装下了无边的夜。凉风带着植物的腥味,轻轻触碰人的腿,便踮起脚尖赶走,心里回味着像蛇一样溜过的味儿。山脚屋后,虫鸣叠叠,处在墨水般的黑夜里,仿佛与人间隔着一个时空。这些人给小山村种下了文学,隔不久,又来寻找它的味道。
长东的夜的黑是真实的,万物在这里学会了乖巧,潜伏在黑色君主的裙裾下。东边的山峰矗立穹顶,有几分像支棱起来的卧佛。一声惊呼如裂帛,“看,月光出来了。”抬头东望,十四的月亮清丽地悬在卧佛的脖子边,无声地喷射着银辉。它裹着一层薄纱,君临万山。在它的呵护下,山村更加邈远、宁静,充满了边界感,像生了银霜的老茶堆砌起来。他们拍着月色,借手机保存记忆,还说“终于不负此行”。他们转换成文学的视觉,认为长东之夜缺少月亮就像焖鸭肉缺少姜一样,味道不纯。再一看,月亮离开东山有几丈远了,更靠近他们了。有时它陷入云翳,光却点亮云,云翳有了另一番味道。当它钻出来时,更明亮了,清光似盐撒下,又像毛尖细毫,也像空明的幕布。他们让店主熄灭了所有的灯,把空间留出来,盛大迎接月光。有人手抖,硬拍出重叠的月亮,在朋友圈收割了点赞。摄影也有味道。
坐回圆桌前,这些人沉默了,所有的话题沉默了。他们不需要声音,因为他们的声音充盈无比,讲一句都是累赘。他们在庆幸,身边的一群讲得着的人。他们有过许多朋友,一些朋友丢失了,一些朋友走来了,但是,尽管朋友总是在变换,而文友却一直不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