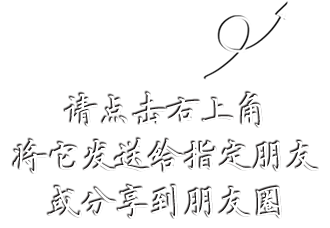□张勇轩
有文曰:关山难越,谁非失路之人;萍水相逢,尽是他乡之客。我想,大概在某种机缘巧合之下,我遇到的都是客家人。
我应该不是一个太标准的客家人,出生的地方还不足以让我沉浸在客家文化中成长。在我十几岁的某一天入乡前,我所理解的“客家”,就只有远离梅州千里之外那条街上,那些用客家话谈笑自如的人;还有就是,每次过年回家摆在年夜饭桌上的“梅菜扣肉”和“酿豆腐”。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叫“客家”,也没有一个地方叫“客家”。“客家”是什么呢?当我开始意识到问题生成的时候,就注定有我明白的那天。
血液有最原始的标记,它从几千年前开始流转于世间,便与千千万万的人连上了关系——那些人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来到了江南,后来在同样的时代再一次徘徊于世。我知道这些是之后的事;爸爸让我明白自己没有高髋骨,也是小时候学不会客家话之后的事。小学语文课本里写到了客家围龙屋,是我喜欢的圆形,简单美观——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客家文化扑面而来,真骄傲!那时候,就像在历史书上看到亲人一样。
客家,客家,客地为家,到哪都是客人。客家人就像背负了使命一样,一个真正的客家人注定是要远走他乡的。生在中原,活在南国,以后我又将流浪到哪里去呢?年轻时也应该像前辈一样,四处漂泊?那天爸爸无意间说道:“你以后应该不会留在这里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客家人就喜欢到处走。”
原来,这就是客家人吗?那是我认识自己很重要的一天,原来感觉那么好,像是醍醐灌顶一样,连空气都像是被洗过一样。现在我也有心走向远方,也许是回故乡吧——其实这与爸爸更久远以前写的诗一样:我也迷茫,故乡在哪里?
在北京漂泊的人心里有个北京,在深圳打拼的人心里有个深圳,在上海挣扎的人心里有个上海。而我的心里有座梅城,那是一座回不去的城,从未到过,却用情极深。我知道我不属于那里,但在我心里她包容了我,生在我心里最荒凉最永恒的地方。
等我开始走向远方之后,也许我会学做梅菜扣肉和酿豆腐,会慢慢学会客家话,会和新朋友说“我是客家人”。等我有小孩时,也会慢慢让他明白自己是一个客家人,告诉他:“孩子,你知道吗?有一天你会去很远的地方。”然后笑笑。也许我还会带他回梅州呢。
谁又知道呢?那么遥远的事情。